
编者按:这是一篇读者来稿。在看到南风窗刊发的《被性侵的儿童,谁能帮他们》后,读者丫丫联系上我们,投递了这篇关于堕胎女性的稿子。

文章中第一人称的主人公,是东部沿海省份小县城里一名妇科医生。在她从医的30年里,为无数女性进行了堕胎手术,她自己也是一名堕胎女性。她理解,堕胎女性常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理状况:堕胎疼痛,因此常年为堕胎女性义诊,进行心理疏导。
当下,在堕胎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的选择。但在主人公30年的从医生涯中,她看多了许多女性因堕胎而背负的心理负担和对身体的伤害。而将这个选择放到家庭中进行考量时,堕胎女性承受的,比身心负担还要复杂得多。

“不就堕了个胎嘛”
我从事妇科工作三十年,是妇科手术室的一名医生,主要负责流产和堕胎手术。
这期间,我接触最多的,是那些堕胎后出现后遗症的堕胎女性。对于她们来说,堕胎手术结束后,真正的疼痛才开始。
我曾经也是一个堕胎疼痛者。1990年8月,我怀上第二胎,胎儿三个多月,但我没有任何察觉。
当时我刚刚成为妇产科医生,忙于工作忽视了自己的身体,又因为生下女儿后,就戴上了节育环,没想到它会在我体内失效。当年计生很严格,我只好做了堕胎手术。

术后,我心里对这个意外到来的孩子放不下,身体上,不经意的一个弯腰,或从座位上站起来,会突然听到体内传来“扑通”一声,好像有什么东西,从我肚子里掉下去。接着就是肚子疼,臀部疼。
夜里,我老是做噩梦,梦里一个小小的人,没有面目也没有手脚,它紧紧地掐住我的脖子。我很害怕,想确认这个小小的人,是不是被我堕掉的那个孩子。
这个念头始终在脑海里盘旋,变成确定的声音:“是他、就是他”。这声音甩不掉。我所有的恐惧与内疚感如同一团毛线,在脑子里缠得死死的,身体的疼痛感也越来越明显。
我的症状持续了近一年,我们医院的一位妇科专家前辈,告诉我这是典型的堕胎疼痛症状,是女性堕胎后的一种应激反应。准妈妈们无法从失去孩子的痛苦中走出,产生深深的歉疚感和负罪感。在她们内心深处,总有扯不去的念头——“肚里孩子奔我而来,我却杀死它,我不配做妈妈。”她们越想,就越疼痛,身体的痛苦到了极限。

之后我学习有关堕胎疼痛知识,并开始接触相关的心理疏导课程,于1995年考取心理咨询师合格证。有了此合格证后,我更多地接触因堕胎疼痛,前来诊治的女患者。
在岗位上工作了30年,2020年,我退休了。退休后,我接受医院的返聘,并建立了堕胎疼痛门诊。但这个举动,在我们县城这个小医院里,非常有争议,尤其是在这所以男性为主导的医院、科室里。当我提出“堕胎疼痛”以及“堕胎疼痛”门诊的想法时,他们不停地在嚷嚷着,“不就堕个胎嘛,至于嘛,还‘堕胎疼痛’?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!”
但我坚持要开设堕胎疼痛门诊,因为被堕胎疼痛折磨的感受,只有堕胎女性能体会。堕胎疼痛门诊,其实是一个堕胎疼痛患者的心理疏导室。这么多年来被她们接纳,并有越来越多的堕胎后遗症女性,走进这间诊室。
任舞是一名堕胎后遗症女性,曾在堕胎疼痛门诊做心理疏导。2021年6月的一天,任舞的丈夫闯进诊室大吼大叫,他说:“本来我老婆堕胎后什么事都没有,自从在你们这里(接受)所谓的治疗后,居然开始哼哼唧唧喊起痛来,这是怎么回事?不就堕了个胎嘛?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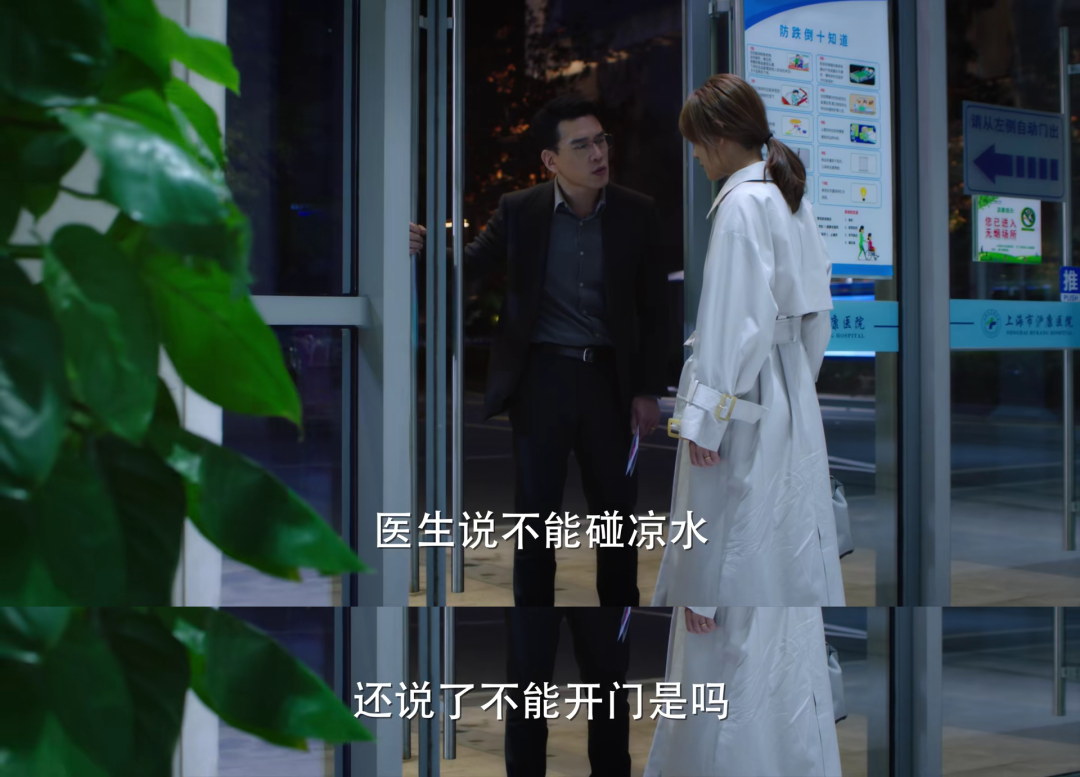
我赶紧劝他冷静有话慢慢说,谁知,他怼我道,“我母亲生四个孩子,也因为政策不允许多生而堕过胎,她都好好的呀。任舞和我结婚后才生过两个孩子,第三胎因为她的身体原因,我同意她堕胎的。她怎么就会有堕胎疼痛了?我闻所未闻这个词,就是你们惯的,给惯出她的这个毛病。”
看着我始终坚持“堕胎疼痛”的说法,他不再理我,返身摔门而去。他去了院长那里,先告我的状,说我是给人乱扣病因的庸医,好好的一个人没病却被说成有病,给人造成生理和心理上的双层痛苦,还给他们夫妻感情带来困扰,他需要院方和我这个“庸医”给出说法。
事后,院长找到我,针对任舞的情况叫我做出合理解释。我心里咯噔一下,难道我的做法不合理吗?但我没有说什么。

“不是神经病”
我在我们医院一直做妇产科医生,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,我给女性做过无数次的流产、堕胎,以及引产手术。我尤其擅长的是堕胎手术,她们要实施堕胎手术的理由有很多,哪怕腹中已经成型的胎儿,也要通过手术清理掉。
我觉得这个手术是不同于任何手术的,连我这个对堕胎手术司空见惯的临床医生,也会不免心惊。当然我在做手术时,是不能有一丝私心杂念的,这都是我手术后的某些联想而产生的。

任舞丈夫来过不久后,任舞悄悄来到医院,含泪向我替她丈夫道歉。
任舞是一个瘦瘦弱弱的33岁女性,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,她于2021年年初怀上三胎。任舞和丈夫是打算要这个孩子的,因为母体体质差以及胎儿发育不全,近四个月的胎儿不得不堕胎。
从上手术台到下手术台,任舞为了腹中的胎儿一直哭泣不止。堕胎手术后,任舞的恢复很慢,在恢复期里她不停地流泪,眼睛出现炎症,之后又出现月经失调,她的周期不规则,发生经期延长的现象,经量不断增加,出血量很大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药补后,任舞以上症状有所减缓,身体情况在好转,但心理上总感觉有过不去的坎,而腹部的疼痛越来越明显。她伴随着疼痛,开始出现幻听,幻觉,睡眠不好,噩梦不断。
在她的噩梦里,老是有个小人儿歇斯底里地哭喊,似乎喊声里有妈妈二字。任舞一次次从噩梦里惊醒,那个小人儿的影子,抹也抹不去。小人儿占据脑袋时,她感觉自己浑身疼痛剧烈。

任舞在最难受时来到我的门诊,那是2021年四月份的一天,她诉说自己的症状。她担忧地问我,自己是不是得了精神病。
我实实在在告诉她,来我这个诊室诊治的人,都是精神因素导致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双层痛苦,但决不是什么精神病。任舞仅凭我的这句“不是精神病”,瞬间释然了。
2014年的冬天,我接待过一位患者,30来岁,从农村坐车过来,她说腹部总是没来由、持续性疼痛,怀疑自己得了治不好的病。我按照常规给她做了检查,没有任何问题。又问起病史,她支支吾吾,说自己曾堕过胎,刚挑起话头,她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
我把她从门诊请进独立的办公室,倒上一杯红糖水,安抚她的情绪。她说起堕胎的经历,夏天的时候她意外怀上老三,当时还没有三胎的政策,家人也不想多一个“负担”,胎儿近四个月大时,她将孩子打掉了。“孩子是被我亲手杀死的。”她哭喊道,认为如今自己遭遇的一切,都是应得的报应。
听了她的经历,根据我的经验,判断她生理上没有任何疾病,患的是“堕胎疼痛”。
堕胎后的女性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,我腹部疼,找不到原因。实际上,这背后是抑郁情绪加重,出现幻觉幻听,心情低落等情况。这些因素诱导了身体的疼痛。

几年前,我接诊过一位患者,她已经转向重度抑郁症,拒绝就医,一只手捂着眼睛,一只手往外推我。她的家属告诉我,她总是不停地念叨说,腹部会胀起来,“自己堕胎的孩子又回到妈妈肚子里”。
据悉,很多堕胎女人在堕胎手术后,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堕胎后遗症。而其中的堕胎疼痛,是后遗症的最大特征。
除此之外,还有月经失调经期延长、宫腔粘连、子宫穿孔、习惯性流产、导致终生不孕等诸多问题。我的自身感受是,堕胎疼痛的影响程度、持续时间等是较长的。而堕胎疼痛在生理和心理上,是双层的,越是疼痛精神就越是紧张;而越是精神上的重压,会越发加重堕胎的疼痛。
这些情绪非常隐晦,不能为外人道,医生也未必能准确判断,以至于耽误患者的治疗。那天在办公室,这位备受堕胎折磨的女性跟我聊了很久,我轻轻抚她的肚子,不断用自己温热的掌心捂住她冰冷的肚脐,直到手心变凉。我将她的堕胎疼痛病症,如实和她说了,并借鉴自己的经历“现身说法”,提醒她这并非是她的过错。

此后连续几个月,她又来找过我几次,每次我都会为她轻抚她腹部,腰部和臀部等。我一边用双手为她轻抚、一边低低发出祈愿的声音,“会好起来的,就会好起来的”。尽管我的声音很低,但其中那种心理暗示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,她们极其愿意接受这个心理暗示。我一点点帮助她重建信心——无论曾经发生过什么,你都配得上更好的生活。
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大约两年多的时间,我和她聊了近50次,前后绵延七十多个小时。最长的一次两个多小时,最短也不少于半个小时,她终于走了出来,今年3月份她告诉我,身体疼痛彻底消失。

绿色的小沙发
我所在的县城医院,患者大多来自农村,在当今生育话题越发受到关注的情况下,乡镇女性群体对于堕胎的认知和接受度,比城市里的女性低很多。在农村家庭和父母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,她们默认了“女人生来就是传宗接代的”、“生孩子是本分”等观念,认为要老老实实生孩子,不能有别的非分想法。
从2014年起,我开始义务为面临堕胎压力的女性提供心理疏导。2020年我退休后,医院返聘我做心理疏导师,并在住院部后院的平房里,开辟出两个房间,作为专门的心理疏导室。做这一切都源于我是个堕胎疼痛患者,我体会过那种双层疼痛的生不如死,找不到“救命稻草”的绝望。我想着,即使自己做不了她们的“救命稻草”,那我就做那一丝光吧。

我的堕胎疼痛心理疏导室,在我们医院后院的一排平房里,其中一间是属于我的心理室。心理室的内部设计,费了我一番心思。在接触过的堕胎疼痛女性患者中,我发现她们的坐姿总是呈蜷缩状,或是双手情不自禁地抱住双膝,或是弓着上身双手抱着自己。这些都是紧张、惶恐、没有安全感的表现,一点都不伸展、放松,看着就叫人心疼。
我特意买小型沙发放在心理室里,它们小小的矮矮的,人坐到里面,会有被环抱的感觉,温暖又踏实。即使她们依然蜷缩着,沙发的高度和宽度,恰好吻合她们的状态。沙发是绿色的,有清新感,窗帘淡淡粉色、轻轻垂落,既明艳又温馨。她们表示很喜欢这个环境,静谧、舒心,又安全。
三年前小禾独自来医院,准备堕胎。她23岁,从外省的一个偏僻农村来到我们县城打工。当时她怀有4个月的身孕。我看见她时,她穿红色羽绒服,缩在窗台角落处抽泣。她的手冻得通红、冰冷,鼻涕水直流。我将女孩扶进办公室,安置好让她坐下,递上一杯热水。
小禾说,她和男友恋爱两年并同居,怀孕后男友带她去见父母。他父母根本看不上她,嫌她出生农村,又嫌她未婚先孕“犯贱”。在这个小镇,人们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,认为女孩“未婚先孕”是极为不光彩的事。

相比之下,男孩家从村里到县城做生意,还买了房,条件不错。男友的母亲将小禾赶出家门,警告他们不准往来,恶狠狠地说:“她肚里的胎儿不知是不是一个野种?”她被这句话刺激,不愿受此羞辱,决定和男友分手。
我问她:“你考虑清楚了吗?男朋友这个人你了解吗?”
她有些犹豫,说堕胎的决定男友不知情,男友坚持要结婚。但她觉得婚姻大事男友做不了主,真正能做主的是他的妈妈。提到男孩的母亲,她又说,“咽不下这口气。”
我感受到,女孩有一时赌气的冲动,便提出与她的父母做一次沟通。小禾很激动,她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,对她的情况知之甚少,她羞于让父母知道这件事。我只好先与她的男友谈话。小禾拨通了手机。我将情况详细说了,电话里男孩态度诚恳,为自己没有照顾好女友道歉,坚定地表示不会让她独自承担。
“你不妨去做一个胎儿的DNA检测,以证明自己和孩子的清白。如果孩子的确是他家的骨肉,你再与他们家谈判婚姻事宜。”我为他们提出一些方法。当然,作为辅导师,我能做的只是倾听,给予心理上的援助,具体困难还要靠当事人自己去解决。

事后,小禾和男友去做了胎儿DNA检测。面对结果,男孩母亲无话可说。但她还在强调女孩家庭条件,不符合要求,“我们不要贫穷家庭”。这一次,小禾没有退缩,向他母亲提出条件,不允许结婚,堕胎必须给予巨额赔偿,走法律程序。最终,男孩母亲妥协,同意儿子和小禾结婚、生下孩子。
领取结婚证书时,他们给我送来喜糖。小禾为自己的孩子赢得了合法性,却因身体原因,没有保住胎儿。肚子里的宝宝五个月大时,做了堕胎手术。今年3月,小禾发给我一个好消息:她已顺产下一个健康的男婴。小禾说,是那个逝去的孩子,为她带来了后续的幸福。她始终感到伤痛,在朋友圈里写道:我很想知道它现在在哪里,一次次希翼与它梦中相逢,却始终未曾梦见它。

堕胎与离婚
在我所接触的乡镇女性堕胎的案例中,有许多是出于感情和家庭不可调和的矛盾,一个很小的点就“引爆”了。
2022年8月,怀孕4个月的小叶,突然攀上家中阳台,要跳下去。她的丈夫眼尖,上去拉扯她,撕扯中小叶从高处掉下来,当场见红。送进医院急救,腹中胎儿已经保不住,不得不堕胎。
她向我求助时,说公婆的这个家她再也不想回去了。小叶结婚5年,丈夫和公婆没有一个不盼她怀孕的,起初还好,帮着她求医问药,到了第5年,他们对小叶生孩子失去信心,讥讽她、骂她,婆婆甚至让丈夫同她离婚。
小叶曾想过自杀,在这种积怨的情绪中,她怀孕了。妊娠期间,家里与小叶的矛盾减少,但感情的裂缝还是难以弥补,婆婆端来的一碗油腻腻的汤,她拒绝了。婆婆不满的嘟囔声被丈夫听见,他冲进房间指责妻子矫情,她瞬间爆发般嚎啕大哭。

孩子流掉后,婆家还想等她恢复后再生。但她坚持离婚不想再复合了。我以治疗手段解决了她身体的疼痛,更深的心理疼痛来源于她不幸的婚姻。漫长的五年婚姻里、在反复的求子无望中,她和家人的感情早已殆尽,即使有了孩子也挽救不了婚姻。
对这类堕胎妈妈群体,她们最需要的是来自家庭的接纳与支持,我个人更期望的是通过辅导,让她的家庭跟她共同来面对。但显然,这对家庭已经无法弥合。
小叶成为我的心理疏导对象,对于她的治愈,是要把她从婚姻纠葛里解脱出来。我找到一位做律师的朋友帮助她,终于使她顺利离婚。
现在堕胎技术很成熟,有药物流产、无痛人工流产、药物流产加无痛清宫,以及引产等方法。安全稳妥,近年来也少有流产方面的医疗事故。流产是一个很小的、平常的手术而已。但小镇的女性,对自己胎儿有一种执念,这些执念或长或短地,控制着这些堕胎女人。

小菲31岁,脸颊瘦削,神色憔悴。她坐在我诊室里,整张脸被泪水模糊。“我这样的人活着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?”她说。
“你年纪轻轻,往后的路很长,能不能遇见想要的都是未知数,难道你不想等等看、试试做?”我安慰道。
她想了想,回答说,“我试试”。我明白她向我倾诉,是她“试试”的第一步。当患者停止流泪,调整好情绪前,我会给与她们一个久久的拥抱。她们痛快淋漓的倾诉就此开始,倾诉是心理疏导重要一环。
小菲是一位堕胎后遗症患者,第一胎因胎儿发育不全流产,这此后留下心理阴影,导致后续不孕。当一个人情绪出现问题,躯体就会产生疾病。她的身体特征为内分泌紊乱,月经不正常。精神紧张或过度焦虑,对脑丘下部脑垂体——卵巢轴产生影响,抑制正常排卵。越是不正常她越是焦虑。
今年2月,小菲再次怀孕,却又因同样的原因流产。这是她第二次堕胎,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,因为有妇科专家预言,她将再难妊娠。小菲近乎偏执,她相信这个预言,又不敢告诉任何人,包括她的丈夫。
事实上,她焦虑和烦躁皆来自于与丈夫的感情,她说她断定丈夫婚内出轨。在公共场合,她亲眼看见自己的丈夫挽着另一个女人的手。她不想结束这段婚姻,害怕自己无法生育,会孤独终老。
我为她感到悲伤,同时表示理解,在农村,许多家庭讨老婆只为传宗接代。这些年我所辅导的案例中,男性几乎没有参与,是消失的。他们或没有责任心或经济不独立。女性独自面对危机,会有许多抱怨和孤独感,感情的事又怎能只有一方付出努力?
小菲还处在纠结中,一边接受我的心理疏导,与此同时,按照医嘱继续服用内分泌的药物。她仍然在祈求能早点怀孕。

与小菲不同,顾真是我辅导过程中遇见的少数职场女性。32岁那年,她在一次与上司的推杯换盏中,犯了错事。她有丈夫有女儿,查出怀孕后,又惊又怕。这块长在自己身体里的肉,她第一时间就想处理掉。
她感到满世界的眼睛都在盯着,始终不敢迈出去第一步,肚里的胎儿一天天增长。就在顾真做堕胎准备时,她对胎儿有了莫名的不舍。她觉得这是一个男孩,在肚子里踢她。我想,这是成为母亲后,女性特有的感受,她给自己暗示,认为与这个孩子有缘。顾真的迷恋与痴狂,以及孕吐的变化,被母亲发现。
母亲逼问出真相,逼她去堕胎,她说要生下这个孩子。那时,她的丈夫恰巧在外地出差,妊娠时间根本对不上,母亲不想让女婿知道女儿的这桩“丑事”。她担心他们离婚,更害怕有“丑事”的女儿以后没人要。
顾真怀孕三个月时,她的母亲给她喂下安眠药,又叫来她的两个姨母,将她绑来医院。在医院,挂号、缴费后,这三个女人合力将她抬上担架车,送入手术室。手术前,她的母亲签了一份保证书,保证堕胎是自愿的,与任何人无关。那时,顾真已经清醒,对于母亲的擅自主张,她不得不顺从。

2013年7月7日,顾真清楚地记得堕胎的日子。在这十年里,她一直郁郁寡欢,已经不能再工作,丈夫知情后,两人最终离婚。
这些变故她看得很轻,甚至不以为然,唯有那个被堕胎的胎儿,是她心里最大的伤痛。“妈妈的心肝、妈妈的肉哟……”她每天不停地给那未见面的孩子写信。
现在,顾真42岁,单身,依靠母亲生活。顾真的母亲向我求助,希望我能开导她的女儿。她对于女儿十年都走不出对胎儿的执念,感到不可思议,觉得她应该有一份正当的工作,有新的感情。顾真的心结,是我在做的课题,她也是我做心理疏导时间最长的一名堕胎女性。
文中人物皆为化名